隋唐兩代氣功的發展
隋唐兩代氣功的發展
隋唐兩代,氣功已經被廣泛應用於治療。此期間問世的三大古典醫籍——《諸病源候論》、《備急千金要方》,《外台秘要》中,都有對氣功的論述。《諸病源候論》中有調息、叩齒、漱口等治病方法;《備急千金要方》中有調氣療病的記載;《外台秘要》中有導引吐納治心腹痛,以及調息法治病的經驗。這些都足以說明,隋唐時期,氣功在醫療實踐中已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巢元方的宣導法
隋煬帝時的名醫巢元方,致力於將氣功在臨床治病時應用。以他為主撰寫的《諸病源候論》,共五十卷,分為67門、1720論。每論列一症候,專治病源,不載方藥,概括了隋以前各家病源學說的研究成果。諸症之後,附有260多種導引吐納的治病法。強調「其燙熨針石別有正方,補養宣導」。
如對「四肢疼痛及不隨,腹內積氣」這一疾病,提出的練功方法是:「床席必須平穩,正身仰臥,緩解衣帶,枕高三寸。握固者,以兩手各自以四指把握拇指。舒臂令去身各五寸,兩腳豎趾,安心定意,調和氣息,莫念餘事,專意念氣,徐徐漱醴泉(口水)者,以舌略漲唇齒,然後咽唾(吞口水),徐徐以口吐氣,鼻引氣入喉,須微微緩作,不可卒急強作。待好調和,引氣勿令自聞出入之聲。每引氣,心心念送之,從腳趾頭使氣出,引氣五息、六息。一出一入為一息,一息數至十息,漸漸增益。得至百息、二百息,病即除愈。」
如上述這類治病經驗,在《諸病源候論》中標為「養生方導引法」。清末廖平將這些內容輯編成冊,近人曹炳章又輯集了續編,書名為《巢氏宣導法》。宣導法的內容十分豐富:從煉意方面來說,有內視丹田、存視五臟、存念、引氣等;從調息方面來說,有練呼氣的、有練吸氣的;從姿勢來說,有仰臥、側臥、端坐、跪坐、踞坐、蹲坐、舒足坐等;從動功來說,有前屈,有旋轉,有頭部活動,有伸展手臂,有屈伸足部等。
宣導法治病,介紹的都是練功方法:
針對「痰飲候」的練功法是:「左右側臥,不息十二通,治痰飲不消。右有飲病,右側臥;左有飲病,左側臥。」
針對「虛勞候」的練功法是:「雞鳴時,叩齒三十六通訖,舔唇漱口,舌聊上齒表,咽之三過。殺蟲補虛勞,令人強壯。」
針對「風痹手足不隨候」的練功法是:「左右拱手,兩臂不息九通。治臂足痛,勞倦,風痹不隨。」
針對「風四肢拘攣不得屈伸候」的練功法是:「立身上下正直,一手上拓,仰手如似推勢,一手向下,如捺物極勢,上下來去,換易四七。去膊內風,兩膊井內冷血,兩腋筋脈攣急。」(山中人案:似《易筋經》摘星換斗勢)
《隋書·經籍志》所載與氣功有關的典籍
《隋書·經籍志》指出:「醫方者,所以除疾疢、保性命之術者也。天有陰陽風雨晦明之氣,人有喜怒哀樂好惡之情。節而行之,則和平調理;專壹其情,則溺而生疢。是以聖人原血脈之本,因針石之用,假藥物之滋,調中養氣,通滯解結,而反之於素。其善者則原脈以知政,推疾以及國。」說得雖然玄乎,卻也不無道理。
《隋書·經籍志》中,歸入「醫方類」的古籍,共有二百五十六部,四千五百十卷。其中不少醫書,與氣功養生、治病有關,例如:
《彭祖養性經》,一卷。
《養生要集》,十卷。
《玉房秘訣》,十卷。
《神仙服食經》,十卷。
《服食諸雜方》,二卷。
《論氣治療方》,一卷。
《靈壽雜方》,二卷。
《龍樹菩薩和香法》,二卷。
《神仙服食神秘方》,二卷。《神仙服食藥方》,十卷。
《龍樹菩薩養性方》,一卷。《引氣圖》,一卷。
《導引圖》,三卷。
《養身經》,一卷。
《養生要術》,一卷。
《養生傳》,二卷。
《帝王養生要方》,二卷。
《素女秘道經》,一卷。
《徐太山房內秘要》,一卷。
從上述有關典籍中,可以窺知隋以前古代氣功發展的概要。
智顗傳有「止觀法」
隋代高僧智顗,人稱「智者大師」,為佛教天臺宗創始人。他在浙江天臺山建立居舍,研究教義,實踐修行。他與晉王楊廣關係極好。楊廣任揚州總管時,曾經請智頷前往揚州傳戒,智顗為楊廣授菩薩戒,楊廣受智顗以「智者」稱號。
智顗不僅對佛教教義闡述得深刻入微,著有《法華經玄義》、《法華經文句》、《摩訶止觀》;他還傳有「止觀法」,其中調身、調息、調心,也就是姿勢、呼吸、意念鍛煉的方法,後世練功者大都採用。他提出的數、隨、止、觀、還、淨的「六妙法門」(註),對除去雜念、誘導入靜,有明顯的作用。
智顗還提出,用「六字訣」治五臟之病,這對後世有一定的影響。北宋官方編纂出版的《聖濟總錄》說:「若五臟之焦壅,即以六氣治之……噓屬肝、呵屬心、呼屬脾、顗屬肺、吹屬腎、唏屬三焦……大抵六字瀉而不補,但覺壅即行,本髒疾已即止。」《聖濟總錄》的觀點,宜將「六字訣」用於實證。明代傅仁字所著《審視瑤函》中,將「六字訣」運用於治療眼科疾病,如治綠風內障等。元末明初的百歲老人冷謙所著的《修齡指要》中有一首《四季卻病歌》:「春噓明目木扶肝,夏至呵心火自閉,秋呬定知金肺潤,腎吹唯要坎中安,三焦嘻卻除煩熱,四季常呼脾化餐,切忌出身聞口耳,其功尤勝保神丹。」
孫思邈將天象和人體相對應
被尊為「藥王」的唐代著名道士孫思邈,在養生學、醫藥學、煉丹術等方面都有傑出的成就。他的醫學理論,建立在「天人合一」的觀念上,根據自然界的災異現象來解釋人體疾症,希望找到病變的根源。他在所著《千金方》中,闡述了不少氣功經驗,著名的有:「存思法」、「迎氣法」、「吞津啄齒煉精法」,以及動功「天竺國按摩婆羅門法」、「老子按摩法」等。
孫思邈享年一百零一歲,這與他氣功鍛煉有素有關。他很看重「存思」,指出:「閉目存思,想見空中太和元氣,如紫雲成蓋,五色分明,下入毛際,漸漸入頂,……,透皮入肉、至骨、至腦,漸漸下入腹中,四肢五臟,皆受其潤;……意專思存,不得外緣,斯須即覺元氣達於氣海,須臾則自達於湧泉,則覺身體振動,兩腳顗曲,亦令床坐有聲拉拉然,則名一通……則身體悅懌,面色光輝,鬢髮潤澤,耳目精明,令人食羨,氣力強健,百病皆去。」
孫思邈還著有《攝養枕中方》,其中導引、行氣兩節,是專講氣功的。書中認為:「氣息得理,即百病不生;若氣息失宜,即諸屙競起。善攝養者,須知調氣方焉,調氣方療萬病大患。」從上述理論中可以知道,孫氏對呼吸鍛煉極為重視。他在書中不僅指出了調息的作用,還介紹了練習呼吸的方法。」
成玄英提倡自我精神解放
唐初受封「西華法師」的著名道士成玄英,對養生學的發展有很大的貢獻。他在學術上以注疏《老子》、《莊子》頁聞名天下。老莊思想對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,使他更注重實際,而不去追求神仙道教的長生久視,也不去追求靈魂在彼岸世界的超升。他謀求自我精神的解脫,達到身心俱泯、物我兩忘的境界。在他的眼裏,世間萬物都是虛幻的,只不過是因緣會合的結果,沒有什麼自為自在的物體。因此,他得出這樣的結論:人去追求物質是虛妄愚蠢的,只能為幻象自尋煩惱。
從這一理論出發,成玄英在注疏《莊子》時說:「觀察萬有,悉皆空寂。故能虛其心室,乃照真源。」由於萬境虛幻,所以人的精神可以不執不滯。從氣功的角度來講,就是使人的精神處乎高度放鬆的狀態,使自己從各種束縛中解脫出來。在他看來,一切困擾人的是非、得失、榮辱、生死等,都是自尋煩惱、傷害身心的邪魔。成玄英主張從身神同一於無的角度,去混合人天,混同物我,便可以得天然解脫。他稱能體悟「人天無二」(即天人合一)境界的人為「真人」,也是他標榜的修道的最高境界。其實,從氣功養生的理論來說,能達到「人天無二」的境界,便是高層次功夫,誠如成玄英所云,「死生不能繫,憂樂不能入」了。
很明顯,此論的思想核心,就是在現實世界尋求自我精神解放,讓人處於一種無憂無慮的境地。應該說,這是一種立意很高的氣功養生觀,對人的身心健康大有裨益。
司馬承禎坐忘於修性
唐代道士司馬承禎,在京師聲望甚高,唐玄宗直呼他為「道兄」。但他卻不戀塵世的富貴榮華,長期隱居天臺山,以松風為娛、野鶴為伴。在氣功養生方面,他注重坐忘宅神,修養虛氣。他的理論是:長生是神仙之道的根本,而長生的前提是養氣。人在先天稟受了「虛氣」,這便是人的「真性」。「真性隔於可欲」,原與塵俗是不相染的,而以道為本。但是,人都會受到後天外物的影響,「遂與道隔」。倘若放任自流,就會盡失真性,從而形損神傷。不過,只要「信敬」坐忘之法,便能克服這一切對身心不利的因素。
什麼是「坐忘」呢?《莊子·大宗師》作瞭解釋:「隳肢體,黜聰明,離形去智,同於大道,此謂『坐忘』。」這是說要順任萬物大化,無復存彼此之別;而且要摒棄思慮機心,自全真性,也就是『斷緣』。做到了斷緣,也就不會去胡思亂想。因為色相是思想意念派生出來的,「色都由想耳,想若不生,終無色事。若知色想外空,色心內妄,妄心空想,誰為色主」?既找到了病源,修道者便不難斷緣:「學道之初,要須安坐,收心離境,住無所有,不著一物,自入虛無。」
司馬承禎從修心復性的實踐經驗中,總結出一套坐忘的氣功養生法,以人的「真性」作為純淨無染的本來品德,通過坐忘洗去塵俗對這「真性」的污染,使人的身心不受引誘和傷害。然而,他又指出,硬要心中無物,那麼「還是有所,非謂無所,凡住有所,則自令人心勞氣發,既不合理,又反成疾」。因為自以為心中無物,但實際上並非「真覺」。司馬承禎強調心中無物是一種意境,但不能執著地追求它,因為一旦執著,心中即已有物。所以他說:「遂我自然,勿為邪見所凝滯,則成功矣。」
作為一個氣功養生家,司馬承禎是當之無愧的。但他同時又是一個道教思想家,他系統地提出要輕方仙道術、重修性之學,就是基於世俗社會的黑暗、罪惡而得出的結論。他還撰寫了《坐忘論》,主張自信、修心、真觀、泰定。坐忘,就是要還我一個清虛自在的人,這就使道教思想發展史上有了一個新的突破。
吳筠著《玄綱論》
唐代著名道士吳筠,是一位氣功理論家。他自稱是「總括樞要」的《玄綱論》,對氣功的闡述十分精闢。《玄綱論·元氣章》指出:「太虛之先,寂寥何有?至精感激而真一生焉,真一運神而元氣自化。……萬象之端,兆朕於此。於是清通澄朗之氣浮而為天,濁滯煩味之氣積而為地,平和柔順之氣結而為人倫,錯謬剛戾之氣散而為雜類。自一氣之所育,播萬殊而種分。涉化機,適變罔窮。然則生天地人物之形者,元氣也;授天地人物之靈者,神明也。」吳筠這個論述,既有道教傳統的認識,也有自創新意的地方。他認為。人是稟元氣而生的,所以人的品性才質等差別也都是由於先天所稟之氣不同而形成的。
基於上述理論,吳筠將人分為睿哲、中人、頑凶三品。睿哲之人稟得純陽之氣,天生惠和,不必教化。頑凶之人稟戾陰之氣而生,無法對其教化,「猶火可滅不能使之寒,冰可消不能使之熱」。「中人入道,不必皆仙。是以教之先理其性,理其性者必平易其心,心平神和而道可冀」。至於治理性和情的方法,吳筠是將這兩者對立起來,聲稱「性本至凝,物感而動」;外物誘惑寂然不動的性,能夠產生情,情悖於道,任情會離道越來越遠。「性動為情,情反於道,故為化機所運,不能自持也」。
吳筠強調的心性煉養,是從氣功的角度來考慮的。一個追求名利的人,是無法得道的,全性修道就是要恬淡無欲,所以吳筠說:「道不欲有心,有心則真氣不集;又不欲苦無心,苦無心則客邪來舍。在於平和恬淡,澄靜精微,虛明合元,有感必應,應而勿取,真偽斯分。」作為一個道士,他也追求神仙長生,而他的長生方法,就是以全性守元為前提。《玄綱論·同有無章》指出:「性全則形全:形全則氣全,氣全則神全,神全則道全,道全則神王,神王則氣靈,氣靈則形超,形超則性徹,性徹則返複流通,與道為一。可使有為無,可使虛為實。吾將與造物者為儔,奚死生之能累乎?」這真是將氣功修煉與神仙長生之道融為一體了!
吳筠的仙道學說,在唐代重視外丹,煉製長生仙藥之風,盛行的時候,卻重視精氣神的內丹修煉,指斥外丹為捨本逐末,對後世道教內丹(即內丹功法)的發展有一定的影響。
士大夫流行服氣、靜坐
唐代的一些士大夫,也有人進行服氣、靜坐等氣功鍛煉,從而使氣功養生、治病,在知識份子階層逐漸普及。
王維是唐代著名詩人、畫家。他中年奉佛,作品頗多禪意。例如,他所作《秋夜獨坐》詩云:「獨坐悲歎鬢,空堂欲二更。雨中山果落,燈下草蟲鳴。白髮終難變,黃金不可成。欲知除老病,唯有學無生。」詩中寫時邁人老,感慨人生,斥神仙虛妄,悟佛義根本。而這首詩,正是在孤獨空虛、潛心默想中寫成的。他從自己嗟老的憂傷,想到了「黃金不可成」,指出了煉丹服藥祈求長生的虛妄;而對坐禪卻竭力推崇,認為坐禪能消除人生的悲哀,解脫生老病死的痛苦,清除七情六欲,才能得「無生」。這「無生」的境界,對於佛教來說,是滅寂;對於氣功來說,是一種高深的階段,身體如浮雲輕飄,幾乎沒有了「自我」。
白居易是唐代最著名的通俗詩人。他晚年居洛陽香山,號香山居士,經常靜坐修禪,頗有心得。他所作《靜坐》詩云:「負暄閉目坐,和氣生肌膚。初飲似醇醪,又為蟄者蘇。外融百骸暢,中適一念無。曠然忘所在,心與虛空俱。」詩中描寫了練功入靜時的舒適狀態,如沒有親身實踐,是寫不出這樣的意境的。他還寫了《在家出家》一詩,其中有「中宵入定跏趺坐,女喚妻呼多不應」的句子,描繪的是靜坐入定後的情形。
柳宗元是「唐宋八大家」之一,與韓愈等倡導古文運動,因而在文壇享有盛名。柳宗元對氣功服氣法相當有研究。他曾寫了一篇《與李睦州論服氣書》,指出當時的一些「服氣書多美言」,是「不可傳之書」。如果照著這些書去練,沒有明師指導,只會帶來有害無益的結果。他還一針見血地指出:李睦州「由服氣以來,貌加老,而心少歡愉」,就是因為「用斯術,而未得路」。柳宗元在批評不科學、不正確的服氣法時,並不否定服氣的養生作用,所以評論是很公允的。
(註)
本人網誌「練功札記」(練功心得)廿一及廿二曾介紹「佛門氣功----六妙法門」,請參考。
本人曾跟太極宗師之入室弟子及
北京氣功師學習,練功近四十年。
願教授 :
(1) 健身氣功---八段錦、
易筋經、鶴翔樁、
丹田呼吸法及運轉法、
大小周天功(內丹功)等
(2) 楊式太極拳及用法、
太極鬆功、太極樁功、
太極推手、太極拳內功等
功用----減輕壓力、對抗抑鬱、
增強免疫能力、延年益壽、
可作自衞用途、開發人體潛能。
特點----功法自然、安全、符合科學,
收費大眾化,時間有彈性。
個別教授,迅速見效。
(十年間已教二百多人,包括醫生、護士、
高級警務人員、消防員、高級行政人員、
商人、科研人員、社工、文員、教師、學生、病人等
筆記以電郵寄送,方便溫習。
只在屯門黃金海岸任教。)
電話預約:
5963 2671 (此手機有
what's
app)
5963
2671
梁先生洽
電郵:
lsw123456@gmail.com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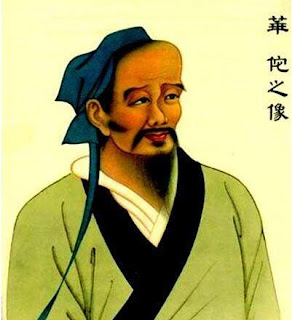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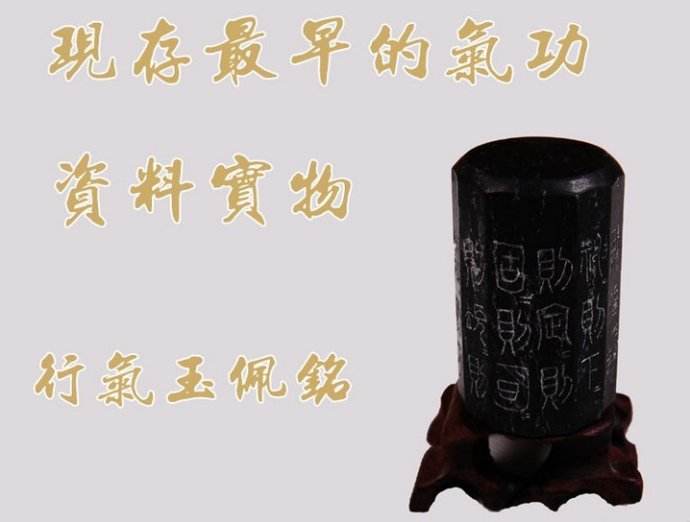
留言
發佈留言